兄长凯旋而归时,小贝正蹲在河道边哭,一边哭,一边摇晃着姐姐。
姐姐死了,肚皮凹陷地死去了。村子里已经很久没有收成了,谷仓见底后,兄长随人去外面搬救兵,再也没有回来。姐姐日复一日地带小贝外出觅食,挖河床,刨鼠洞,翻草根。河水蒸干这天,姐姐也蒸干了,她靠着河滩上的石冢,把最后几只蚂蚱递给小贝,说她累了,要歇一会,让小贝吃了东西再去转转。等小贝带着兄长失而复得的消息小跑回来时,她已经躺倒了,双眼落满灰尘,不再眨动。
哭累了以后,小贝背起姐姐。他的肚子叫了起来,吃下的蝗虫来埋怨他抢占了姐姐的生机了。他回到家里,把姐姐轻轻放在父亲怀中,轻手轻脚,像在安置一片羽毛。原本喜庆的氛围顿时暗淡下去。母亲嚎啕大哭,父亲则无声落泪,兄长带来的神婆也念起了咒语,在村民的沉默中为逝者送终。
过了一会儿,归来不久的兄长走上前,搀起父母。
“人死不能复生。”他轻声说。“而且,这样一来,咱们就有活路了。”
“来,把姐姐埋了吧。”
神婆念完咒语,兄长示意小贝去取铁锹,等万事俱备,便开始指挥村民安葬死者。眼前的兄长和出发前不一样了,身材变壮实了,眼神变得像鹰,看谁都像猎物。小贝不喜欢这副模样。从兄长那里,他觉察不到感情。姐姐死了,兄长甚至都没有流泪,仿佛她只是个随处可见的陌生女人。就连她的死也仿佛在兄长的预料之中,尽管按照他的说法,这不过是个不幸却又幸运的巧合而已。
遵照兄长的指示,村民把姐姐埋在了村子中央。神婆在此作了一夜的法,披头散发,将试管和培养皿中的溶液浇灌在坟头。巫术只对新鲜尸体有效,这是人们从神婆的疯言疯语中解读出的说法。
夜半三更,起风了,仿佛要下雨,但是到了第二天,土地却依旧龟裂纵横。绝望的村民们再度聚集在姐姐下葬的广场上,要向兄长讨说法,争执间,发现坟头生出了一棵树,枝丫稚嫩,却执意要同上苍对抗,不到半个时辰,树冠下已能供人乘凉。兄长说,这就是他找回的法子。在漫长的求索中,他走遍每一座困顿至死的村镇和城市,最终倒在海床上等死。就在那时,疯疯癫癫的神婆出现在了他的面前,救活了他,接着,在昙花一现的清醒时段,告诉了他这个拯救家园的办法。
又过了一天,大树开花了,花瓣有白有紫。小贝认得它们。干旱尚未来临时,姐姐会调皮地给他编小辫,然后在上面缀满雏菊和丁香。从神树的性状里,他看到了姐姐的影子。而神树也迅速回应了他的印象,一夜过后,褪去满树繁花,枝叶间生出累累硕果,每一枚果实都和婴儿时候的姐姐一模一样。
兄长摘下了一个姐姐,张嘴咬下一口,却被母亲劈手打落在地。
“你做什么!”她反手又是一巴掌。
“妈,放心——这是水果,只是长得像人。刚回来的时候,我不是说了可能会有点吓人吗?别担心,没事的。”兄长说完,又摘下一个来,塞给旁边的村民,自己则捡起地上的,掸落尘土,吮吸起腹腔里脏器形状的果肉。
接过果实的村民左顾右盼,最后闭上眼,咬了一小口,接着是一大口,然后吃掉了整条手臂。看着他大快朵颐,其他人也终于按捺不住腹部的阵痛,争先恐后地狼吞虎咽起来。
最后,小贝的父母也屈服了。他们摘下了果子,一边哭,一边吞咽。小贝也加入了他们。他接过兄长递来的娃娃果,咬了一口,唇齿间顿时清香四溢。死去的姐姐在他的嘴里复活了,像夏季的阳光,如砂糖般甜蜜。小贝又哭了。在河滩上觅食时,他曾经许诺过要守护姐姐,如今他却把誓言吃下了肚,只是为了活下去。
童年结束了。
盛宴临近终止时,兄长让小贝收集四散的果核和种子。
“我要再出去一趟,去附近的几个村子,把这些带给他们。”他说着,摸了摸小贝的头,“我知道这种方式很难让你接受,毕竟那是你的姐姐。但世界就是这样不讲道理,如果有别的办法,谁想这样呢?”
那也是你的姐姐。
小贝本想这样说,却只是埋头攒了一捧骨殖,装进兄长撑开的口袋里。临走前,兄长还嘱咐村民都装些果核,回家种在地里。所有人都照做了,其中也包括小贝的父母。小贝本来还想再做些什么,来纪念这个被姐姐拯救的日子,但是饱食感引发的困倦却淹没了他,让他在回到家后不久,便在母亲的怀里沉沉睡去了。
树上没有果子了,光秃秃的。骸骨形状的果核,和果皮外的毛发间镶嵌的种子,都被悉数埋进地里。手舞足蹈的神婆已经不知去向,在失踪前,曾经口吐白沫地嚷嚷着:第一个牺牲的人,将会为所有人带来救赎。如今这救赎已经来临,人们只要尽本分、遵天命便好。
当晚,小贝趴在炕头,感受着母亲的体温,做了一个梦。梦里,姐姐变成了山一样的巨人,开天辟地,又倒在地上,躯壳幻化成世间万物。他躺在姐姐的胸口,看着树苗一粒粒钻出自己的身体,渐渐喘不上气。他在窒息中惊醒,天已大亮,屋外绿树如茵,每棵树上都结满了大大小小的姐姐,乌黑的秀发从土壤里喷涌而出,如黑色芒草般四处释放着奔腾的生命。他穿好衣服,下地去帮父母耕田。梦境却不依不饶,在他的裤裆里留下了一滩湿漉漉的成长印迹。

小贝的村子地处盆地中央,交通闭塞。树林发育这段时间,兄长遍历附近村落,最终,再度翻越环绕盆地的群山,进入不为村民所知的世界。
兄长直到入冬才回来。在此期间,小贝一直在精心呵护每一棵树。日夜吞下的果实凝结成沉甸甸的原罪。只有站在树下,看着树苗们茁壮成长,他才能获得片刻安心。在他的呵护下,树上的姐姐们渐渐长成了妙龄少女。大树和大树之间仿佛心有灵犀,让果实们维持着神秘的年龄同步。
兄长回来时,小贝正在给姐姐们套过冬用的棉袄。棉袄是他用乌发草织的,比棉麻穿着更暖和。四十五,四十六,四十七。他正在清点人数,忽然听见鞋子摩擦草叶的声音,便转过身来,刚好看到兄长带着十几名陌生青年赶向村中大屋。他上前问候兄长,兄长却叫他别说没用的,叫村里的人一起来。他腰间别着长刀短刃,额角多了两道伤疤,衣着变华丽了,眼神却变得更加阴郁。身后的青年们也大抵如此,身材壮硕,遍体鳞伤,比小贝更像兄长的孪生兄弟。
在大屋里,兄长彻底变了。小贝印象里的兄长少言寡语,忠心耿耿,为了家人,只管埋头苦干。但是眼前的兄长却面朝满屋父老乡亲,侃侃而谈,不时喝口水,环顾四周,像是在确认谁是自己人,谁不是。
兄长端坐在长桌一侧,开始讲故事,说他带出去的树种和草籽一出盆地便不管用了。这些植物只能种在村子附近,离村子越远,长势越差,等翻过山脉,就再也不出芽了。好在他在路上遇到了运输能力高强的商人联盟,后者愿意帮忙把姐姐树和乌发草的衍生产品运输到更远的地方。为了配合他们,村民们需要做的,只是建设工厂,规模化各家正在进行的耕种作业,从而让姐姐树更加高效地发挥作用。
村民们咀嚼着兄长描绘的愿景。一些人品尝出了其中的血腥,向兄长投来敌视的目光。他们身上的乌黑长袍和胯下新鲜的实木座椅却出卖了他们,让他们在兄长的扫视中缓缓垂下头,不再多嘴。
“世道已经变了,如果我们不这么做,大陆上很多人都会死。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。我们活了下来,我们有责任让更多人也活下来。这是我们赎罪的方式。”兄长把手掌压在刀柄上。他的语言收买了一些人,他的手收买了另一些人。他带来的年轻人守在门口,冷漠地注视着屋里发生的一切。
“接下来我会交代我的计划,不过在这之前,我想看看有多少人愿意加盟。”
兄长再度扫视四周。屋里起先一片沉默,过了一会,一只手举了起来,又一只手举了起来,然后是第三只,第四只,渐渐超过半数。
“好。我不会为难剩下的人,你们可以走了。”
一些没举手的人离开了,一些没举手的人留在了屋里。小贝本想上前问兄长他到底怎么了,却被兄长身边的随从推了回去。兄长对此并不加以阻拦,甚至对那人点头以示认可。小贝对此感到骇然,旋即感到心灰意冷。他随家人走出屋外,走了一会,猛然跪在地上,呕出半口未消化的果子,从此下定决心,不再过问兄长的任何行径。
从这以后,兄长便在村子里住下了。他不再回家,而是在村外圈了一块地,在那里风餐露宿。
在大半个村子的帮助下,他们迅速建好车间,和随后赶来的商队代表进行接洽,完成了第一批样品的展示和交付。交易现场,他们带来了一箱脱骨果脯,一桶鲜榨饮料,还有用果核、草叶和原木制成的桌椅板凳。商人们很满意,带走了全部货物。贸易路线走通了,工厂从此日夜轰鸣。人们从树上摘下一批又一批姐姐,扒光外衣,装箱送进工厂。村子渐渐被分割成两个区域,一个区域果树林立,另一个区域血肉横飞。园丁们剪断果实头顶的脐带,将她们成批运往车间。车间里的工人则负责抽取体液,剥下果肉晾干,再挑选出符合规格的骨骼、皮肤,送到加工区域,最终将它们制成食物、砖瓦、日用品和奇形怪状的首饰。产品一部分被村民自行消化,更多的批次则被人打点整齐,交付给前来取货的商人,带到外面的世界去。
兄长还在继续讲故事,这些故事比以往的那些更加隐晦,但个个掷地有声。诸如他在处决工贼与侵入者时的愤慨指控;诸如他在拥立新村长时的激昂陈词;诸如他在热情款待渐渐渗透进村落的武装商队时,在宴席间,在宅屋后发出的窃窃私语。
这些故事风暴一般席卷整片盆地,把越来越多的人吹向兄长的阵营。低地果园的消息也随之蔓延开来。陆续有逃荒者翻山越岭来此定居,皈依在兄长的麾下。他的工厂规模越来越大,包围了自由人的林场。一些新入伍的佣兵开始僭越兄长曾经划下的界限,在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。目睹这一切,小贝时常感到自己脚下已不再是坚实的土地,而是无底深渊。一股愤怒自深渊中徐徐升起。他觉得兄长背叛了姐姐,村民也背叛了姐姐,只有他才是姐姐真正的守护者。姐姐是他的,只有他配得上她。他渐渐陷入偏执,疑神疑鬼,开始日夜守在林间,逢人便撵,每晚都做着关于姐姐的梦。
他打着只属于他的战争,与此同时,另一场战争正在暗中酝酿。小贝看不见这场战争的蛛丝马迹,看不见森林里游走的人影和根系间埋藏着的斧钺钩叉,看不见他家人向兄长俯首称臣的场面,也看不见他兄长仍旧阴沉凌厉的面容。他看见的只有姐姐,树上的姐姐,树下的姐姐。
在夜不归宿的时光里,他建起一座林间棚屋,携带全部家当住了进去。姐姐的照片被他装裱在姐姐做成的相框里,相框被他放在姐姐做成的橱柜上面。餐桌上的碗筷是用姐姐烧制成的,盘子里的肉是姐姐的心肝和肠胃。姐姐,姐姐,姐姐,姐姐。在这灰褐色和肉红色交织的空间里,姐姐辐射出的生命力令小贝如痴如醉。他偶尔会在林间睡着,耳边回荡着姐姐的呼唤,醒来以后,凉风习习,少女们在头顶轻轻摇动,仿佛一串串起舞的风铃。
春天来了,夏季去了,兄长的计划随着秋日临近,渐渐成熟。
靠着一年来的辛苦和忠诚,他请来了商人们的首领,还说服了他,将联盟的根据地从干涸的海角迁至林地。
立秋当日,首领坐在轿子里,口中噙着风干的手指,身后旌旗猎猎。漫长的交接和转移工作已经结束。在前往新家的路上,他终于得以深沉品味口中少女的味道。万灵凋敝前,他曾吃下数不清的美食,上至皇家御膳,下至虫豸蛇蝎。对美味,他早已没了概念,就连服用自己的亲生骨肉也无法带给他的舌头任何快感。但是少女的体香却唤醒了他的味蕾,让他开始幻想:在旅途的终点,究竟有何等珍馐在等他享用。这幻想令首领老去了,变得和善了,在得到小贝兄长的热情接见时,也只是慵懒地靠在太师椅里,任由眼前这踏实稳重的年轻人安排一切,自己则靠在主宾席上,笑纳下属呈上的一份份贡物。
宴席行至中途,一只手扳住了首领的下颏。他伸手去抓它,口中涌出大股金属味道。一只手把匕首缓缓送进他的肚腩,另一只手则持刀割开他裸露的喉咙。首领的一生就这样随着尚未被他消化的食物飞散开去,一部分飞向天空,另一部分涂在地上。早已倒戈的侍从们履行了叛徒的义务。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迅速爆发,又迅速结束。末了,兄长摘下已故首领的戒指和项链,装点在自己的身上,站在焚烧尸体的篝火前,开始讲述他在第二次离开盆地以后,被商队俘虏,卧薪尝胆的复仇故事。他列数商队的罪状,始于他们在贫瘠末世上的掠夺行径,提到了自己为了不让盗匪般的联盟掠夺盆地而做出的牺牲,赞赏他身边这些和他同甘共苦的兄弟,并感谢长久以来一直配合他推动这场计划的所有人。而在最后,他宣布:由商人中饱私囊的旧秩序已经解体,他将组织联盟的残余力量,用更加有效的方式拯救芸芸众生。
他的演讲结束时,大地忽然剧烈颤抖起来,在翡翠海似的丛林深处,一棵树发了疯,枝杈开始向四面八方凶猛冲刺,转眼间便鲸吞了半片林场。树与草的根割破土地,钻进群山深处。它们的枝干合而为一,形成一棵前所未见的齐天建木。这不是计划的一部分,但兄长仍旧对惶恐不安的听众说:此乃吉兆。
他看到了人群中的父母,唤他们来他身边,问他们小贝在哪里。带着对这已然陌生的救世主的困惑和无力,父母二人遥指建木方向。于是兄长明白了:眼前景观乃是小贝的造物。他向人群高呼小贝的名字,说新世界的诞生也有自己弟弟的一份功劳,然后在欢呼声中回到据点。
等到夜深时分,他带上灯笼、匕首和贴身侍卫,前往密林深处。
建木的根系错综复杂,俨然一片墨绿色的迷宫。枝干排山倒海向他们挤压过来,乌黑细密的草叶纠缠起众人的脚掌,让他们在披荆斩棘中渐渐耗尽体力。尽管如此,兄长却依旧稳步前进,而他的侍卫们也无声无息地跟在身后,保护他们的主人。
风渐渐弱了,树根盘曲成树洞,阻隔了空气的流通。一名侍卫注意到上方的果实形状有异,便举高灯笼,陡然看见一串白皙脚趾悬挂在头顶。他心头一震,灯笼掉在了地上,引得一行人纷纷驻足。他们这才注意到,少女们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凹凸有致的少妇,身材丰满,面容圆润。越过这些悬挂在树洞顶端的饱满人形,他们还看到了树皮上的朵朵花纹。花纹中雕刻着女孩和男孩嬉戏打闹的场面,一幅幅图景绵延向前,引领众人来到建木中央的巨大空洞。在这里,吃奶的女孩,采花的女孩,跳舞的女孩,耕作的女孩,飞翔的女孩,潜泳的女孩,出嫁的女孩,女孩生下的女孩,以及和她们做着或相同或不同事情的男孩们,肩并肩,手挽手,千千万万,纷纷扬扬飞向树洞上方,消失在洞顶的一方星空里。
兄长站在洞穴中央,环顾四周。一向擅长讲故事的他,反常地陷入了沉默。他没有向侍卫们解释他沉默的原因,侍卫们也任由他私藏他的秘密。他们在沉默中回到据点,让今晚的所见所闻成为各自心中的谜题。
他们没能找到小贝。在先前的革命里,他们也没能救出神婆。
天亮了,对夜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的世人们渐次醒来。他们不知道革命背后的成功与失败,只是在这个与旧世界不尽相同的新世界里把兄长奉为主宰,一如既往地向主宰提出期待,也迎合主宰的期待,将姐姐树的血肉播撒到更远的地方。大陆虽然还是那个河涸海枯,一滴雨也不下的大陆,却久违地喧嚣起来。而在喧哗声传不到的地方,那终究没能找到的小贝,渐渐变成了一段民间传说。

(未完待续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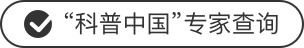



 扫码下载APP
扫码下载APP

 科普中国APP
科普中国APP
 科普中国
科普中国
 科普中国
科普中国